
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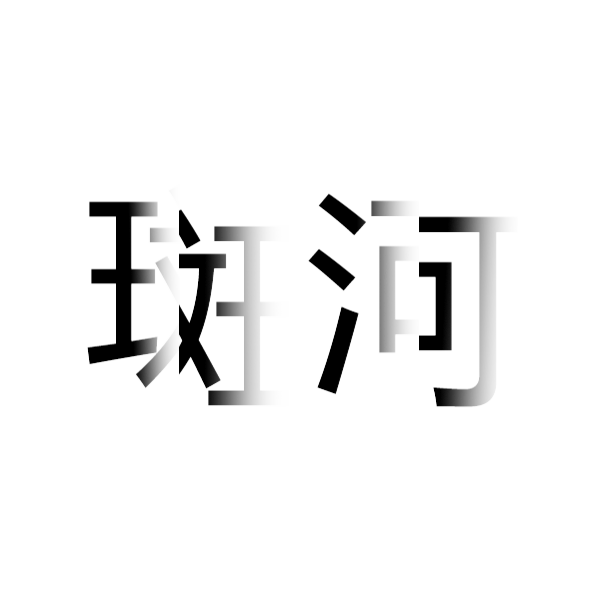
《祝福》中的人分三类:以四叔、婆婆、大伯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代表了剥削者,以祥林嫂、短工为代表的被剥削者,和一个笔墨极少的“另类”——以“我”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就是“新党”。三者之中,“革命党人”似乎应当是最活跃、最能动的角色,但全文之中,“我”仅仅作为观察者出场,对全文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冷视着剥削的过去式与进行时,以至于无聊到“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逃避,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不负责的“革命者”形象了。这暗示着作者对“辛亥革命对社会毫无影响”的戏谑讥讽。在“我”这个“革命者”出场的些许戏份里,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个所谓的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到革命者的先进性,用语上,“我”已不再避讳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在“我”与短工的短暂对话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
“什么时候死的?”
“怎么死的?”
很明显,相对于“老”的避讳,我脱口而出对“万不可提及”的“死亡疾病”无所忌惮,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迷信。这是革命者在用语上的进步性。其次,在同情之心上,革命者对祥林嫂也有所怜悯: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这个动作极耐人寻味,要知道,在一个孩子都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的鲁镇,能对祥林嫂伸出援手的“我”是多么难得!然而这个行为又多么让人不爽:在我们眼中,如果“我”是共产党员,那必须得冲上前去,拉住她的手,一边叫着“老妈妈”一边分出自己的粮食给她,甚至计划为她谋一个住处。但“我”没有。首先我默认她是一个乞丐:“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也默认她是来找“我”讨钱。作者明明可以直接写:“多年未见,祥林嫂已经是一个乞丐了。”然而鲁迅没有,他依靠“我”的眼睛来“看”祥林嫂枯败的外表后,用一个巧妙的冒号,总结出了“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结果。“分明”、“已经”、“纯乎”,三个词六个字,字字写着“我”的肯定,“我”是那么高傲而冷漠。所以“我”只是“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连多走一步都不愿意:万一她不来呢?万一她就这样倒在我的面前呢?“我”还会给她钱吗?换言之,“我”对祥林嫂的帮助,是否仅仅到“钱”的层面为止了?如此看来,“我”的形象,辛亥革命革命者的形象又近乎伪善,但给予“我”至少停下脚步,愿意给钱这两个行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是看客们没有的,超越了“看客心理”的进步行为。
但更多的,鲁迅写尽了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上极不彻底的变化。
首先,“我”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心极强,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在祥林嫂发出“地狱三连问”时,“我”支梧搪塞着,用着“我说不清”含混过去后,“乘她不再紧接着问,迈开步便走,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觉得很不安逸。”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麻烦”,“我”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并没有细问祥林嫂问地狱的原因,反而狼狈逃走。心里不觉得祥林嫂是太苦了才发问,而是因为她是疯子才发问。回到家后又自觉不安:又觉得自己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怕祥林嫂自杀,这回就全然不是怜悯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这就好比用鞋拍死臭虫又怕臭虫尸体粘在鞋上——祥林嫂之死会带给“我”秽气。但“随后也就自笑……”说着“本没有什么深意义”,又道:“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本质上,对于祥林嫂,我更多的是追求“毫无关系”这种冷漠的关系,“我”在辛亥革命后对被剥削者的冷漠没有变。在第三十二段,“我”在认识到祥林嫂是“陈旧的玩物”的情况下,仍大言不惭地叫到“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祥林嫂之死,反而成了一句轻松的“还不错”,且“一面想,反而渐渐舒畅起来,“我”的形象竟冷血无情起来。
其次,“我”作为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表,仍然向封建统治阶级投怀送抱,体现出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我”在得知祥林嫂“老了”之后,出于隐隐的内疚,曾多次想问四叔祥林嫂之死的详细情况,但反而退缩了:“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明明知道“老了”是“死了”的隐语,但“我”却不敢问,其本质原因就是后面一句话:“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也是一个谬种”,以至于被吓到“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寻求逃跑。这就是一个辛亥革命革命者的残缺的地方:面对强大的封建强权,不愿坚持探求真相,反而选择逃避,让祥林嫂之死变得极模糊不清,连死也无法被“正名”而流落到短工口中的一句:“还不是穷死的?”其实何尝不是呢?祥林嫂若富贵,情形一定会大变,正如《我不是药神》所言:天下只有一种病,穷病。当然,这都是另谈。“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投怀送抱还体现在“我”被封建环境的腐化,并对封建统治阶级体现出羡慕,在最后一段,“我”面对迷信的“祝福”,感到“懒散且舒适”,与三十三段“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相呼应,“我”被“祝福”的热闹气氛所腐化,直到“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完完全全忘却了祥林嫂,放下了心中的内疚包袱,完全得到了自我安慰,“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麻木在迷信的“祝福”里,最终还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同化。
所以辛亥革命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它有声却无力,正如《祝福》开头那声“雷鸣”,“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说不清,理不透,只能是一声钝响:闷沉、乏力,窝藏着希望,包蔽着绝望。
- 标题: 钝响
- 作者: 张知丙
- 创建于 : 2024-11-08 00:00:00
- 更新于 : 2024-11-13 22:52:46
- 链接: https://patchyriver.github.io/读后感/钝响/
-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 斑河文学,禁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