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 雨 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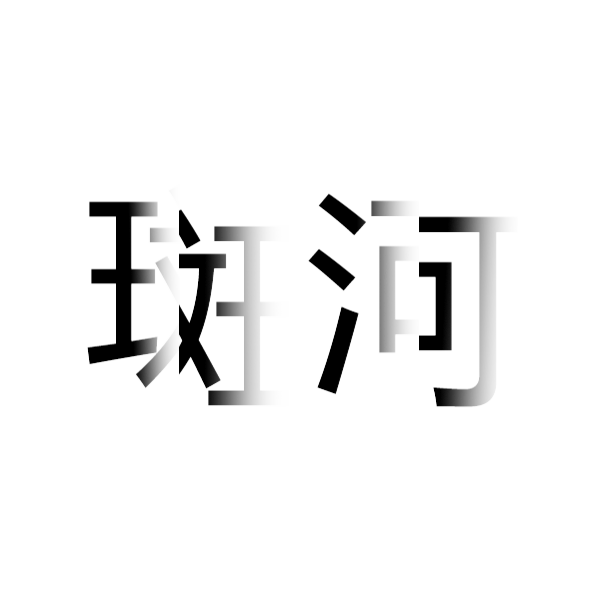
鱼,是离不开水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渝,他为数不合所记得的,是他的名字。关于它的来源,他依稀记得——他出生
时风雨大作,闪电映出了他的身形:畸形的脸、微跛的右腿,这可是天生的灾兆,于是等他稍大些,父母就带着他去算命,那算了一辈子命的老先生皱了眉,叹声气,转身拿出一张圆形纸片来,捉笔写下水字,又在旁边画了一条鱼。父母似乎会了意,急忙给他买了条鱼,小心养在盆里。“渝这个名字也是那时取的?”“没错。”街巷里一堆人叽叽喳喳的说。
此时渝坐在那破旧的草屋里,又想起些往事来:夜,一个雨夜,他的母亲抱着他狂奔,一滴滴流淌在他蒙住脸的布,渗进来的,是水?是泪?还是?他记不清了,高烧烧坏了他的喉咙,只记得母亲说:“雨后含有彩虹的。”然后只剩雨在哭、水在诉。他来到这个小镇,在篮子里,边上放着盆,盆里游着鱼。“本以为是个江流儿,没想到是个死残废!”“哈哈哈。”人们大笑。
渝出了门,走的路一如千百次之前:他初来这,抱着他的鱼,冒着雨,淌过水,在溪边的草屋
落脚。可过于漫长的雨季里,每滴雨水都被拉长成一段深深的叹息:他又饥又饿,只得用布蒙上
脸,去街上试图找到一丝生机。他像一只老鼠窜在人群中,像沉入水中的一粒墨,荒度、急促、迷茫
“咚!”一个挑担的伙计不慎砸中了渝,渝一个不稳,似滚似飞地来到了一家茶馆门前,像学艺不精的舞狮者,似一个被抽飞的陀螺,一团黑布在一群“之乎者也”的文人前颇为荒谬——最终那用以遮羞的黑布也散落在地。旁人的目光齐齐聚在渝上,无论商人、伙计、文人,万籁皆寂,甚于他梦中雨水的凉。这小小的墨彻底地被水吞没了,被旁人一瞬爆发出的大笑淹没了。
“然后呢?”人群中有人问。
“这个傻子,看我们都笑了还以此为荣呢!看他那张脸,哈哈哈……”
“看,那傻子来了!”“走走走!”人群涌动,雨又开始下……
头,层层叠叠;人,密密麻麻;声,喧喧闹闹。越过人挤人,渝在一块长木板上“舞蹈”——更应该说是尽力地行走,他的日常成了他们的笑料:他变着花样,走、跑、踱……人群又爆发出一阵大笑,这声似乎可以传到胡同里最深最高的院子
渝很欢喜,他甚至带了他的鱼一起“表演”,人们笑,他也笑——由于他的嘴角肌肉异常,他笑起来也像哭丧着脸,破损的、像台老旧的织布机,吱、吱。
渝的表演结束了,他像舞步似乞怜的动作引得“好心人”纷纷投给他几块食物,其中一串冰糖葫芦晶莹得亮眼,他想,这也许就是母亲所说的彩虹。逾一扑,一跌,把它牢牢护住。同时,人群散去,忙他们各自的事去,即使他们一如既往的一事无成。
此时,远处深巷高墙里,窜出一个人来,不必猜,定是那小孩被渝的表演吸引,厌恶墙内幸福却乏味的生活,出未找乐子了。他在酒旗、商摊间灵动前进——像渝,但终归不似渝。
顿时双方的目光对视,像日见了月,夏遇见了冬。渝笑,把糖葫芦递出,。小孩在高墙里哪见过这东西,他的眼里,先是错愕,次是好奇,一口咬下,只余满足。
可是渝没有在意,那男孩的瞳中,一丝惊恐闪过,那纯真的眼里,映出了,一个男人,高大的男人,正举起右拳。
“唔。”一声闷响,渝像断线的木偶摔了下去,本就残废的右腿无力支撑,连他右手抱着的盆也飞了出去,水洒了一地,缺水的鱼左右扑腾,发出剧烈的啪啪声,但随即融化在小贩一成不变的叫卖里。渝有点恍惚了,他想抓住那条鱼,但其伸出的右手又被男人狠狠踩住。渝的手和鱼一样,忽地动弹一下,便再无反应。
“天好像又黑了……”渝想,有什么东西顺着耳根流下 ,“是雨吗?但什么时候,雨成了咸的呢……”
耳鸣间隙,有些低语,低雨,“我都和你说了,别和这种祸害玩,回去读书!”
“可是……”
“走!”
冰糖葫芦落地,渝试图抓住——但一如既往,他抓不住母亲、抓不住鱼、也抓不住自己。视野里的最后一抹红也消逝,只余黑白,次是灰,最后是黑。天黑了。
渝消失了,可人们并不在乎,还是按部就班地生活。
不知多久,渝被发现在草屋里,嘴唇干得龟裂。可懂医的人说,他是窒息而死的。
倘若,雨后没有彩虹,城堡里没有童话,倘若,倘若……
可是鱼,纵使哭泣,但为什么不会说话呢?彩虹为什么只有黑白两色呢?
- 标题: 鱼 雨 渝
- 作者: 昀儒
- 创建于 : 2024-11-08 00:00:00
- 更新于 : 2024-11-13 22:34:02
- 链接: https://patchyriver.github.io/散文/鱼 雨 渝/
- 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 斑河文学,禁止转载。





